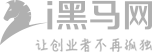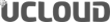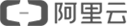BAT已是赢家,我们在微信和淘宝上停留的时间(Spending Time)越长,马化腾和马云们就越高兴——我们真实的生命长度越少,贡献给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就越多。
但狂欢的背后,却鲜有人注意到,现在是“新年”。这个最悠闲的假期,原本是对我们每个人辛劳一年的最大奖赏,但我们却始终低着头,成了手机红包的奴隶。
今天将作者阳光的这篇文章送给大家。正如他所说,“生命本应是一场有自身目的的旅行,我们大多数人却都容易沉湎于智能手机这样的一些并不重要的物质世界里,虚掷光阴。”
所以,BAT已是赢家,我们在微信和淘宝上停留的时间(Spending Time)越长,马化腾和马云们就越高兴——我们真实的生命长度越少,贡献给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就越多。
文/阳光 学者
编辑/王瑞 崔婧
2013年初春笔者徒步峨嵋山巧遇一位行脚僧,只见他单棍背着衣箱行囊,行色匆匆,心无旁骛,快步如飞,眨眼间就消失在白雪深山之间。生命本应是一场有自身目的的旅行,我们大多数人却都容易沉湎于智能手机这样的一些并不重要的物质世界里,虚掷光阴。
每个人忙忙碌碌了一年,仿佛就是为了等这一个节日。
春节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胜过了圣诞节对于西方人。后者庆祝耶稣的诞生,关心的是一个陌生的神性世界(天堂与地狱),中国人的春节是世俗的、充满快乐的,它关心的是自己过去一年的收获和来年的幸福。
这个最悠闲的假期,是对我们每个人辛劳一年的最大奖赏。可是,在春节这七天“最短的假期”里,你准备好“信息斋戒”了吗?——换言之,你是打算陪着家人晒晒暖阳聊聊天,打打麻将享受天伦之乐,或约三五好友去爬爬山、踏踏青,还是依旧紧握手中的iPhone、iPad和时尚一体机,继续做这些电子产品的“奴仆”呢?
小明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
早上7点半,他一边翻看手机,一边吃早饭;
8点到9点赶地铁,百无聊赖的时间,只能通过手机打发;
上午10点和11点左右都是工作间歇,他会查查朋友圈谁发了信息,QQ和陌陌上有没有人打招呼;
中午12点半午睡之前,还要检查一遍手机上的信息;
下午3点和4点的工作间隙,他一样通过看手机来放松;
5点到6点下班后坐地铁,还得靠手机打发时间;
一天里最惬意的是晚饭后的泡脚的时光,小明不用赶急,一边仔细检查一下朋友圈,就怕错过任何一个好玩的信息,一边还要点个赞什么的,逐条翻看再加转发,这常常要花费他半小时多的时间。
11点半,小明在依依不舍地最后一遍翻看手机,毅然决然地关掉手机上床睡觉。
这一天,小明共查看了10次手机,累计用时1.5个小时左右。
小明是谁?是你,是我,是我们身边许多“手机依赖症者”的群像素描。
根据2015年1月27日腾讯发布的《解密微信——首份微信数据报告》,55%的微信用户每天打开微信的次数和小明一样,都在10次以上,即便以每次平均5分钟计算,这意味着近6亿微信用户中,有3亿多人每天平均仅花在微信上的时间就接近了一个小时!如果再加上“今日头条”、QQ、手机游戏和手机购物等在内的其他移动应用在内,中国近7亿只能手机用户中,近4亿用户每天花在手机网络信息服务上的时间不会低于1-2个小时。
腾讯最新发布的微信用户行为分析报告,每天打开微信30次以上的“重度用户”高达4分之一,也就是说近1.5亿人
小明还不算电子产品的重度用户。我身边的一个朋友每天在朋友圈转发的文章都在15篇左右,我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把她每天转发的所有文章都通读一遍,至少需要1个小时,而且整个手机屏幕瞬间全是她的转发文章,忍无可忍之下,我干脆将她直接删除。
根据腾讯的微信用户行为分析报告,6亿微信用户中,近20%为微信依赖的“重症患者”,即19%的用户每天会打开微信40次以上,如果除去一个人正常的8小时睡眠时间,这意味着这些用户每过20分钟,就要打开微信看一眼,唯恐错过了什么宝贝!
对这种手机依赖症患者,费洛伊德描述的儿童恋物癖好行为就能解释了这种心理上的病因——一般来说,两三岁的儿童经常喜欢玩具车游戏,如果玩具车出现了,他就会拍手称快,因为“妈妈”(玩具车)就在身边!一旦玩具车跑开了,他的妈妈缺失症就会引发轻微的焦虑(玩具车在他们眼里就象征了“妈妈”)。对于一部分沉迷于电子世界里的成人来说,手机就是我们刷存在感的最好玩具。
经常喜欢刷微信朋友圈的,还容易患一种叫做“错失焦虑症”的心理疾病。比如,如果你不幸受邀加入了某群,其中有一阔佬心情大好或者很不爽时动辄就抛撒红包取乐,这时你该怎么办?是24小时坚守朋友圈守候那只兔子的出现呢?还是每隔5分钟上去逛一逛?我们在使用智能手机之后,总是害怕失去那些蜂拥而来、大多却毫无价值的信息,喜欢在那上面虚掷感情和时间。
你还生活在“第二媒介现实”里吗?
手机本来只是人们一个偶尔使用的联络工具,现在却成为我们须臾难离的“拐杖”。
按照技术文化学者刘易斯·芒福德的研究,在1850年之前,人类在交通和通信方面的困难,意外地成为我们过滤垃圾信息的天然过滤器。可是,随着更多电子通讯设施的发明,人们通过电子设备接收到的外界信息,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处理能力,以致于一个人的时间花费变得异常分散,大多数时候想独处一室而不被打扰,也变得非常困难。
比如,在电报电话没有发明之前,我们接到来自遥远地方的紧急信函时,才会下定决心亲自出行。信息传递的困难,同样决定了我们的行动速度相对缓慢,这使得那时的社会交往大多限于个人和个人之间,而且是可控的。可是在今天,随着实时通信的出现,这种天然的“过滤器”消失了:电视、报纸、PC、智能手机每时每刻都在争抢着,吸引你的注意力。
“人们收到的外界信息越来越多,就越来越难以吸收或者应付周围环境的任何一个单项信息,更不用说去应付整个信息环境了。”小明在被微信所吸引的同时,吃早饭时,他再也体会不到食物的滋味和留意家人的脸色;上了地铁,再也看不到身边人群和当天社会环境的变化;即便在单位,他也会更多留意手机上的信息,而不是和同事去面对面交流;到了家里,他更只能依靠手机来打发时间,更别说和家人一起讨论问题,或者去看一整本书的信息了。
按照芒福德的研究,在人和机器的相互适应过程中,机器对人的要求控制越来越多,但人类如何应对机器的能力并没有增加多少,结果是,外部世界对于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强烈(且不论这种要求是否重要和合理),而人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忙乱、越来越弱、越来越差。人们“不再有主动选择,只有被动吸收”。
事实上,今天越来越严重的手机依赖,使我们更加深陷在“二马”包围的虚拟世界里,从网络社交到网络购物,我们在微信和淘宝上停留的时间(SpendingTime)越长,马化腾和马云们就越高兴,我们真实的生命长度越少,贡献给他们的时间和金钱就越多。更何况,现在连“三马”(马明哲)也要打破头皮抢着要进来搞联合,他们三个非要掌控每一个人中国人的生老病死,给我们提供端到端的“人生整体解决方案”!
生命如白驹过隙,每逢春节这种危机意识会更加强烈。可是“三马”依旧希望通过掌控我们的时间和消费,为每一个中国人从生到死提供一揽子的“生命整体解决方案”,让人们从此时时刻刻停留在他们设置的快乐而空幻的虚拟世界里
在传播学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由书面语言到电子信息构成的世界叫做“第二媒介现实”,它和真实世界的最大区别是,如果你手里紧紧攥着一把泥土,你就能闻见泥土的芳香和感受到手中泥土的细滑,如果你读到陆游的诗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那只是大脑里对应的反应区才能唤醒对对于“泥香”的一种记忆而已。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和蒲松龄笔下的众多“狐仙”们,就是这样让我们沉醉不知归去的、虚假的“第二媒介现实”。
著名媒介学家沃尔特·翁曾经指出,口语时代的人们更倾向于社群化交往和培养外向的人格结构,而不像书面文化时代的人们那样偏好于内省活动,口语交流容易使人们实现群体的团结,而阅读和书写行为都更像是孤零零的个人活动,使人的关注焦点转向自身。到了电子时代呢?在虚拟世界中众声喧哗的数字狂欢里,我们往往是最害怕寂寞的、昏黄灯光下蜗居在客厅沙发一角玩弄手机的那一个网络幽灵。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鸿燕传书的年代,我们还有种种关于爱情如何美好的想象力和回忆画面,在陌陌式的滥交网络空间里,我们却只有“姐飘过,只是一个传说”的贫乏和苍白。
你有多久没有去青草地上打个滚、撒个野了?或去嗅一嗅松针叶上的树脂香味,听听松涛的低吟浅唱了?春节到,七天很短,放下你的手机,和春天来一个最亲近的约会吧!
本文作者阳光,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记录、观察与研究,研究领域包括网络社会、数字媒介和媒介融合等,主要作品有《纯粹关系——网络分享时代的社会交往》、《网络英雄传》、《新浪模式》等。作者邮箱:sunrise2000320@163.com。 欢迎订阅其本人的微信公众号“人在网络”。
本文不代表本刊观点和立场,如需转载请联系微信korcha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