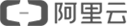平台化运营的核心KPI与品牌化运营的KPI又有着天然的差异性,平台化运营的核心在于“高成长”,在于“增长势能”所带来的对供需双方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的成长。
从本质来说,对商业项目的判断逻辑是可以穷举的,跨行业创业者或投资人尤其清楚这一点,即根据底层商业判断框架即可对绝大多数本质为商业类的项目做高效初筛,再结合特定行业的差异化洞察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价值判断。
倘若以“供给”和“需求”去审视教育行业“创业”和“资本”的关系,我们将看到,有许多创业项目正有悖教育行业的底层商业框架而行,他们是被资本热潮催生出的“供给”,其目标是去满足资本方的投资“需求”。资本繁荣之下,之所以产生大量泡沫,正是因为其脱离了“可穷举”的商业本质和行业洞察。这些泡沫项目的产生有的是因为创业者及投资人的认知及判断力缺失,也有的只是“供需”双方在资本热潮下贪欲释放所依托的载体,这些都可以概括为“原罪”。
这次,我们一起剖析下曾红极一时的K12领域的“平台化教育创业”的“三宗罪”。
“原罪”一:平台化教育模式对用户核心需求的严重误判
平台化模式对用户的教育需求的核心——“教学供给”到底带来了什么价值?标准化的回答是:平台可以整合更多、更广泛的教学供给,从而给用户提供更多选择。
客观地说,平台化整合“供给”是高效的商业选择,但却是对用户的真正需求的极大误判。在教育行业,用户普遍不掌握选择标准,而试错成本又极高,因而对用户来说,同时展现大量供给实则是一种选择灾难。其实,用户真正的教育需求是“可控的”、“标准化的”、需要较低判断力即可识别的优秀教学供给,而这些不是平台化所能赋予的。
“原罪”二:平台化教育模式对“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超低控制力
“低频信息需求,高频服务需求”,教育行业这一特点对于平台化模式来说是一大噩梦。之所以平台化模式在电商及其他服务市场能够成功,其核心原因在于——这些市场的用户需求属于高频需求,另一原因是平台在需求和供给方对接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话语权,因为供需双方在对接前均处于黑盒当中。平台模式的供需两端越零散、链接度越低,平台的生存和议价能力则越高,这些特点在淘宝和滴滴打车等模式上都可以看到。
反观教育行业,用户需求的产生几乎按年计次,但用户的服务频次却很高。同时,教学服务依赖于老师个体,这些特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平台对供需两端的把控力,一旦通过平台对接上,供需双方完全能够脱离平台进行之后的持续交付。基于以上原因,平台化的教育模式在需求对接完毕后就几乎不再存有价值;而且,当用户需求被满足后,用户口碑传播的是核心价值提供者即老师,而不是平台模式的运营商。以上这些,对平台化教育公司来说,都是很悲伤的故事。
“原罪”三:灾难裂变,当平台化教育模式的“不经济”遇上平台化的“高成长”原生需求
所有商业模式可被规模化的前提都是其最小商业单元是“可经济”的,也就是可赚钱的。在教育行业,“可经济”的价值考量可以具化为每个用户的潜在“生命周期价值”,这一价值主要通过单次交易利润、用户潜在交易频次来体现。
基于上文说到的,平台化教育模式对“供需”双方的低控制力导致其无法从用户潜在交易频次中获取商业利益。同时,因为用户信息需求频次低,所以平台缺少足够大的需求总量(需求总量=用户数*信息需求频次,平台缺少信息需求频次的乘数效应),因而其对供给端没有持续的高议价能力,这也就使得平台很难从每个用户需求产生的单次出售中获得“经济的”(对标平台运营成本来看)交易利润。综合来看,平台化教育模式在每个用户身上可挖掘的商业价值是“不经济”的。
从另一角度来看,平台化运营的核心KPI与品牌化运营的KPI又有着天然的差异性,平台化运营的核心在于“高成长”,在于“增长势能”所带来的对供需双方的影响和控制能力的成长。
一方面面临最小商业单元“不经济”,另一方面则是平台化模式对“高成长性”的原生需求,团队在此两难境地中最终将被“高成长性”所迫投入大量资源去打造不可持续的商业黑洞。而在这条路上,教育用户的核心需求也将与企业的短期及中期业务目标渐行渐远。至此,平台化教育模式在商业端与用户需求端都将逐步远离真正的价值建设。
对于创业,我们强调创新、效率,但更加需要强调基于“深度思考”的商业认知和行业洞察。创新企业关于企业“核心目标”的定义应该是来自更加深入的、面向用户需求的思考。商业效率的提升不应该成为企业所定义的“核心目标”,而应该成为满足用户真实需求的“实现工具”。对于任何体量的公司,定义问题远远要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而定义正确问题的能力将会是市场上永久的稀缺资源,特别是在资本所催生的繁荣期。
注:本文作者是致优教育创始人及CEO任洋辉,系投稿。任洋辉为前学大教育高管,创业前曾作为投资人投资过多个教育类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