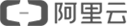颇具创意的“死亡体验馆”为何遭到市场冷遇?两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丁锐又是如何萌生这个“另类”创业想法的?
文 | 智晓锋
去年清明节,经四年筹备、花费400多万的“醒来”死亡体验馆正式开张迎客。
这是一间由10个空间组成的封闭式体验馆。参与者要就游戏题目展开辩论探讨,并“投死”一名同伴。淘汰者会在一台模拟焚化炉中“归零”,最后“醒来”。
(*“醒来”死亡体验馆)
经营效果没有达到创始人丁锐的预期。他本想做成“百年老店”,但顾客抱怨、人流不稳定等问题接踵而至。投入的400万元已无法收回,盈利更是遥遥无期。丁锐说,“醒来”会在明年清明节关门。
颇具创意的“死亡体验馆”为何遭到市场冷遇?两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丁锐又是如何萌生这个“另类”创业想法的?
创业家&i黑马最近和他聊了聊。
以下为“醒来”死亡体验馆创始人丁锐口述,经创业家&i黑马编辑:
有钱后的折腾
1997年,24岁的我跟大我两岁的姐姐借了10万块,在杭州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主要接一些电视台的业务,不久后就还清。这十年间,作为乙方的我,过得并不开心,特别烦。在将公司整体以100万元卖出时,还有30多员工。
尽管那是个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期,我并没有赚到多少钱。我的收入主要来自其它方面。在2000年初开始,我每个月能获得100多万的净收入,持续多年。
如果用攒了很久的钱去买辆车,人应该很高兴。但如果随手就能买一辆,可能只会高兴一秒钟。我就是出门吃碗拉面的命,不抽烟不喝酒,还能干嘛?就只能精神危机了。后来整个人都已垮掉,做什么都不高兴。
“折腾”能摆脱这种状态。2008年,我来到上海,开始学心理学。学习期间,我还租了一间150多平米的公寓房,全部铺上榻榻米,开了个免费的道场。我想知道各种各样的人对生命的看法。
自从一名讲《道德经》的老师在这开讲,带来不少听课的人之后,每天来道场的人就络绎不绝。有来听儒家的,也有来唱颂歌的。两年多时间里,大概有200多名老师在这里讲过课,每次讲座约三四十人。
2010年,我又创办了众筹网站“觉”。和那些在传统行业发过财的老男人一样,我的新生意也想跟互联网有点关系。但我的眼光和控制力不行,就交给一个看起来很活泛儿的男孩打理。然而,前期投入的100万不久后就打了水漂。
我不甘心这笔钱就此不见。这就像赌博一样,感觉还有希望,就再扔更多钱下去。我又找来一位产品经理,他踏实能干特别有理想。一直到2015年,我已投资1000万元。这支十几人的小团队一直没有散,靠接活来养自己。但从创业的角度来说,项目已经死掉了。我只能承担由莽撞和自以为是带来的后果。
在这期间,“觉”曾寻找过投资,由团队里的其他人参加路演。坦率地说,我不去路演是害怕失败。钱有点像玻璃罩子,会改变一个人的心理,使你不必过多与外界接触。尤其是那些在传统行业成功过的人特别固执。其实不怪他们,他们太害怕那个被保护的东西(会失去),里面其实非常脆弱。
上个月,我报名参加了《奇葩大会》的海选,从300进80中胜出。没想到做过那么多演讲的我,会在一帮90后面前紧张。现场6人一组,依次做自我介绍。我直接紧张到声音发抖。回头想,之所以紧张是因为在那个场合,我剥掉了所有之前穿上的盔甲,必须面对一个未知、可以决定命运的评价体系。那一刻的慌张,令我记忆犹新。
一旦知道自己害怕什么,你就会有的放矢地去测试自己的害怕。只有那些害怕的东西,才会让你有生命力。
做死亡体验馆
我和做临终关怀服务的老黄(创业家&i黑马注:“醒来”联合创始人黄卫平)就是在道场认识的。2011年,我也加入他开始做临终关怀。
做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在想,是否能有一个地方让大家来聊聊死亡?一开始,我只想做一个真实的焚化炉,给体验者带来感官刺激。因为一般人对死亡的认知就是肉体的死亡。
在这期间,我和老黄经常跑殡仪馆和火葬场,和入殓师成为朋友,还躺过真实的焚化炉。那是火葬场的焚烧炉第一次“烧”活人。尽管知道技术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戴着口罩刚躺上去,我就紧张起来,肾发空。当鼓风机吹起,炉子里飘满骨灰时,我有一种快窒息的感觉,脑袋有一阵子的空白。
我还考虑过其它实景式设计,如设置有意外死亡、疾病死亡、衰老死亡三道门。以色列有一家衰老体验馆,体验者穿上防护服会步履维艰,眼睛渐渐模糊。韩国的一家死亡体验馆就是躺进棺材,体验者要读遗嘱。然而,这些只是形式上的死亡,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代表社会身份的死亡。
实际上,人会经历四个阶段的死亡,身体、心理、社会关系以及灵魂的死亡。死亡是这四个合在一起的结构体。在临终关怀中,这个结构体很难真的被系统化解决。
从2011年开始筹备,到2012年租下房子开始装修,去年清明节,“醒来”死亡体验馆终于开门营业。
“醒来”是一间由10个空间组成的封闭式体验馆。每次体验以12人为一组,时长约3小时,玩12轮心理游戏。每轮参与者要就游戏题目展开辩论探讨,并“投死”一名同伴。淘汰者会穿过“无常”之门,走入“彼岸”,在一台模拟焚化炉中“归零”,最后“醒来”。
与“狼人杀”这类游戏不同,你在“醒来”没有一张身份牌,你就是你自己。这个游戏的第一轮尤其惨烈,你看谁不顺眼就可以直接将其投出去。而投某个人可以有各种各样恶毒的理由,比如,觉得对方脸色阴沉,或者看起来总是跟他自己的女朋友秀恩爱。有领导腔的人最容易被高票投死。
这相当于他的社会身份死亡。实际上,这比肉体的死亡更让人觉得紧张。
这12轮题目,囊括了亲情、友情、爱情、权力、财富,以及孤独等人生中的12个关键词。游戏设计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本能。我们先有一个开场的题,价值观的冲突。在这轮自我介绍结束后,游戏的设置需要马上“投出你最喜欢的人”,就是现场体验者认为谁最有眼缘。被赞美的人自然很高兴。接下来,“投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这个人要站在12个人当中。
直接让他走吗?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游戏变得没那么有趣。
我们会给他一个活下来的机会。其他所有背对着他的人,可以把椅子转回来。如果超过半数的人转椅子,这个人就可以挑另一个人替他去“死”。
有一次我是主持人,有个姑娘被投“死”了,之后超过半数椅子转了过来。这时,一般人会选择挑一个不转椅子的人“去死”。这姑娘却挑了一个离她最近,并且是第一个转过身的人。我感到很诧异,就追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说,没有转身的人是真诚的,他们把自己的恶意保持到底,而转过身的人可能是伪善,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表演了他的善意。她说,“如果是伪善,我送他去‘死’,如果是真善,我也让他知道,善良是有代价的。”
她表达了人性当中非常真实的那个部分。很多人都是浮皮潦草地在表达善或恶。经过这几次转折,你会发现体验者都是如履薄冰。
困难重重
我不建议生活中认识的人来玩,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现实中的关系。这个游戏撼动的,远非我们最初所想。
有一名HR曾集合了他们公司的人来体验。一开始大家都投这位HR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是组织者,大家也没玩过这种游戏。到中间轮时,他却作为最虚伪的人被投了出去。于是他整个人很抓狂、崩溃。回到公司,面对的是一群认为他最虚伪的人,他该如何自处?后来,他写过多次信投诉我们,说游戏三观不正。
我们曾经尝试做过推广。有点拧巴的是,如果做推广,你想要得到的是团队的资源,光靠散客不可行。但每次做完团队后,都像伤筋动骨一百天。团队的形态跟这个游戏的本质是冲突的。后来我们就拒绝团队。
从2012年开始,我已经为这家体验馆投入了400万元。创办之初,我希望干出一点成绩,做成百年老店。老黄也总觉得押这么一把,没准儿就红了呢?所以“醒来”也有押注的成分。比如,某个大款特别怕死,说给你们捐个什么吧。总有这种可能性。
由于场地原因,“醒来”每天顶多接待24个人,也不可能场场都满。至今为止“烧”了不到4000人。算一下营收,它能维持就不错了,做不到盈利。前期投入无法收回。
我们本来预计清明节会有很多人来,但事与愿违。今年5月份,体验者暴增。但到这周,突然就没什么人来了。我们经常遇到断崖式的高峰低谷。
这是没办法解决的事。它本身切口太小,不是个大数据或大流量的端口。最近,我们开会定了个比较清晰的规划,打算后年清明关门。它是个死亡体验馆,自己也得死。老黄这时又开始幻想着说,现在敲敲边鼓,说不定会有很多人因为要闭馆蜂拥而来,还会吸引几个大款。这不行,你得信守承诺,该死就得死。
太累了。这件事的意义到这里就好了。“累”可能是我找来的一个可以下来的台阶。
接下来,我会继续做线上的事,围绕“醒来”这个探讨生死的IP。我曾经出版过一本同名书,现在正在写相关的影视剧。